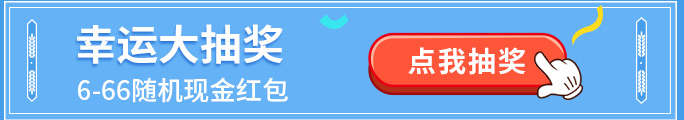数字游民,从工位中解脱
他们曾在10平方米的房车里共处48小时,一起吃饭、工作、睡觉,潘诗宇感觉“空间局促”,通过做瑜伽解压。
频繁移动还带来了漂泊感和某种孤独。由于停留时间短暂,丁锋每次在一个城市遇到新朋友,所聊话题都雷同,“关系无法深入下去”。后来他们放弃房车,选择居住在公寓或社区。
为了结交新朋友,张乐从2018年开始随身携带一个飞盘,每到一个新城市,就在当地社交网站上发帖,组织飞盘活动。他还报过语言、烹饪、艺术类课程,参加过旅行团。有的国家的人不会说英语,他很难交到本地朋友。
“ANDCO”“Remote Year”是美国两家为远程工作者提供服务的市场机构。两家机构2018年发布的远程办公调查报告《The Anywhere Office》显示,超过三成的受访者把“孤独”列为远程工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。
张乐说,很多数字游民的移动频率会越来越慢,从几天换一个地方到几个月换一个城市,最后选择2-3个地方长住。
有的游民家庭还需要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。张乐和“游牧夫妻”都没有孩子,但他们见过一些数字游民,有的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,有的让孩子在家上网课,还有的让孩子在雨林生活,接受生态教育。
潘诗宇和丁锋曾探讨,假如他们有了孩子,不走主流教育路径,孩子是否能适应主流社会。他们还没有答案。
张乐说,数字游民常常要面对来自“传统社会价值观”的挑战,“很多人认为这样的生活方式过于‘非主流’”。他回家后,常被亲戚追问挣多少钱,何时生孩子。
他也曾纠结,在地质学领域已钻研多年,转行做内容是否有些可惜。但他觉得,人应该做喜欢的事情并创造价值。
张乐记得在马来西亚看野生人猿保护基地时,遇到一个奥地利人。对方每年放假都来这里看人猿,来了10年了,记得每一个人猿的名字。这名奥地利人启发张乐,“找到让自己舒服的状态,不要跟着别人的指引走”。
丁锋对一对美国夫妇印象深刻。这对夫妇只带1000美元就开始了房车旅行,中途经历了撞车、孩子早产,一度山穷水尽。但他们坚持了下来,穿越了十几个国家。他们靠表演流动艺术、教瑜伽、当外教挣钱,并将此视为一场“连接世界”的行为艺术。
“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有非常强的使命感”,这让丁锋思考,“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,想过什么样的生活。”张乐正在写一本书,想向更多人介绍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。
(责编:薛添翼)